
文、圖/黃致鈞,摘自《紐約學》時報出版
據說紐約公寓太狹窄陰暗,紐約客因此都有一間充當自家客廳的私房咖啡館,三不五時就去那兒消磨透氣,一如影集《六人行》裡六位主角的「Central Perk」。確實,我在紐約也有這麼一處落腳之地,店主還是位法國女子。
我對這家咖啡館並非一見鍾情,她的風格稍嫌不修邊幅,如同自家樓下的雜貨鋪平凡,特別登門拜訪的我因此有些失望,彷彿盛裝出席一場晚宴卻發現不過是一頓尋常的家庭聚餐。反倒是櫃檯後的一位工讀青年令我印象深刻,他是紐約極少會展露真誠笑容並關心客人需求的服務生。
我於是給了這家咖啡館第二次機會,並在那位工讀生推薦下點了一份培根煎蛋三明治。還記得從全麥土司裡流洩而出的蛋黃覆滿生菜和番茄,不禁使我想起臺北巷口的早餐店,從此不定期上門看還會有什麼意外收穫—即使過一陣子那位工讀青年便不見蹤影。
這家咖啡館不是以咖啡為主、餐點為輔的「coffee shop」, 而是反之的「café」。在紐約,要好咖啡去前者,要吃得飽去後者;這家咖啡館雖然名為「café」,咖啡卻有「coffee shop」的水準,有的吃有的喝遂逐漸成為我攝取咖啡因和解決午餐的好去處。
安居澤西市時,我經常拿了讀物搭一站地鐵過河,到這家咖啡館邊念書邊喝咖啡邊用午餐—通常是一份混著蔥花和瑞士乾酪的火腿炒蛋,或者一塊外酥內柔的巧克力可頌—坐到上課前半小時才姍姍離去。搬到曼哈頓後走路到這家咖啡館更只消兩分鐘,因此白天沒事就會帶著報紙、筆電等家當到那兒窩一下午。

公寓附近其實幾步路就有一家café,但餐點選擇都沒有這家咖啡館精彩多樣。天熱沒食慾,可以點盤油醋沙拉;天冷要暖胃,則來碗雞湯配幾片法式長棍麵包;只是嘴饞,一塊他們自家在肉品包裝區烘焙坊烤出的餅乾或瑪芬剛剛好;要控制飲食,一杯現榨任選三種的蔬果汁怎麼搭都好喝。
洋人最愛的三明治到了這家咖啡館也是變化多端,各有合適口味隨季節轉換搭配。混了一陣子,我發現這家咖啡館是一位法國女子所經營,沒人告訴我她就是老闆,但光從走進店裡的架式就知道小姐她不是光來打工的工讀生。
女子來自巴黎,年紀約略四十五歲上下,一頭乾燥深褐的長髮與一身橄欖肌倒像出生地中海沿岸,在金髮白膚占多數的西村格外惹眼。她的雙脣總是塗上兩抹豔紅,講起英文全是嘟在舌尖的濃濃法國腔,「可頌」堅持要發法語原音的「誇聳」。法國女子裝扮時髦恰到好處,秋天穿黑色皮衣,春天著碎花洋裝,經常騎著淑女車來到店裡,有時手中還捧著一束花,彷彿周圍都洋溢著手風琴奏出的香頌。
然而法國女子不是殷勤接待客人的老闆娘,多數時間甚至板著一張臉,一副要吃不吃隨便你的冷漠表情。也因此即便我知道她是店主,她也認得我這張店內少見的亞洲男性臉孔,我們的對話卻始終僅止於點餐;偶爾見她心情好,才硬擠出一絲微笑給我這每週上門至少三、四次的常客。
法國女子的管理模式也有些放牛吃草,尤其當代人早已熟知也認同「分工合作」能發揮組織最高效率,這家咖啡館仍採行工業革命前的線性生產模式:櫃臺後的兩位店員不像星巴克一個接單結帳,一個沖泡咖啡,而是兩人各自從頭到尾服務一組客人,因此「多出來」的顧客便落得工讀生各自忙著切貝果或打奶泡而沒人理睬的窘境。
或許店員必須像八爪章魚什麼都做太勞累,這家咖啡館人事替換頻率非常高,常常幾個月不到又是一群新面孔。老主顧的我也從原先會一個個問名字、打招呼,到後來就當一面之交吧。
某陣子兩位工讀生在這家咖啡館撐了半年之久,總是熱情稱呼我「金」的兩人還興師問罪為何我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就在得知他們分別叫「芬」和「大衛」後不到幾週,一個脫帽不幹,一個被法國女子開除。人力經常短缺下,有時早午餐的尖峰時段就看法國女子帶著先生和兒子親自上陣支援。
縱使如此經營時常造成客人臭臉走掉或者隊伍一路排到門口,法國女子也不以為意,照樣慢條斯理地收銀找錢,或者介紹今天有什麼口味的甜甜圈;更不用談只領固定時薪的工讀生,客人少反而樂得輕鬆快活,大家一起慢慢來不用急。
面對法國女子的直率隨性,資本主義萬萬歲的紐約客也只能搖頭嘆氣。但一如紐約客依舊對巴黎心嚮往之,這家咖啡館仍然散發獨特魅力,無論四季總是生意興隆。
她的餐點分量宛如餵養勞工,有時飽足到連晚餐都省下,質量卻不輸西村那些精緻的法式餐酒館;她的裝潢簡陋甚至稍嫌破舊,牆面卻漆成了鮮亮的橙紅,掛了幾幅不知是拿來展示還是賣錢的藝術畫作;她的桌椅沒釘死,任客人隨意併桌後亂成一團,大家也就肩並肩,你邊啃夾了番茄的比司吉邊看書,我邊吸加了花生醬的水果昔邊讀報,倒也親密融洽;她前前後後二十個座位不到,即便沒有廁所但有免費無線網路和多個插座,曾經愛坐多久都不會有人趕。
這家咖啡館座落西村邊陲,周圍是曼哈頓少見的單純住宅區;又她的外觀毫不起眼,一個沒注意就會走過,上門顧客因此多是附近街坊鄰居,少有特別朝聖的觀光客或短暫歇息的上班族,而我也得以在那兒瞧見幾張在地面孔。

一位應該年近耄耋的老奶奶和我一樣同為常客。所謂能吃就是福,她老人家雖然頭髮已白如雪,食量卻絲毫不遜發育中的年輕人,總是點一份蛋捲配沙拉,然後在附餐的全麥土司抹上一層厚厚奶油,有時還會淋上幾滴蜂蜜增添滋味。白髮奶奶胃口雖好,身材雖豐腴,餐桌上卻一定擺著一瓶橘色塑膠藥罐,彷彿暗示其他客人若她不幸突然倒下,餵食裡頭的藥丸就沒錯了。
白髮奶奶從來不見有親朋好友陪伴,自己倒也過著舒適愜意的小日子,不僅經常試圖與其他客人閒聊幾句—即便冷漠的紐約客大多敷衍虛應—用餐完還會拿出化妝鏡,仔細地替自己的雙脣畫上口紅,再面帶微笑拄著拐杖離去。
另一位老奶奶,頭髮同樣花白,但染成一頭叛逆的湖水綠,還綁成兩根俏皮的辮子,大概是早在六〇、 七〇年代就混西村的老嬉痞。綠髮奶奶總是帶著一本小說配著一杯咖啡和一片餅乾,常見她讀得忘我而不自覺咧嘴竊笑。每每看見綠髮奶奶和白髮奶奶,我總提醒自己老年時也要活得如此怡然自得,優雅自在。
當然,這家咖啡館不只有退休人士。一位身材略為肥厚的壯年男子,總是雙眼緊盯筆電螢幕監控股市走向,而喜歡帶《金融時報》去邊讀邊喝咖啡的我或許引起他注意已久,某次終於忍不住上前攀談。
原來男子自創一家避險基金,習慣在這家咖啡館用餐之際順便掌握最新財經消息。或許認為遇到同好,這位擁有許多人脈連結的基金經理人,隨後還把我引薦給一間分析不良債券的公司,從此在咖啡館相遇也總要聊一下哪國市場不穩定,哪檔債券可投資—縱使金融商品交易根本不是我的專業領域,只能哼啊哈的應付一下。
這位阿爾及利亞裔的男子也是這家咖啡館的熟客,遇到法國女子總會用流利法語交談幾句,但自從相識的那年冬天過後好一段時間沒遇見他。《經濟學人》雜誌曾指出避險基金平均壽命只有五年,我不知道這位基金經理人是大賺一筆出國逍遙,還是慘賠收場忙著變賣家產,但都謝謝他曾經拉拔提攜。
紐約無愧是「機會之城」,在這家咖啡館不只遇到那位基金經理人曾表示要替我和華爾街牽線。
另一位男子,年紀看似而立之年,一頭狂野金髮宛如頂了一把烈焰在顱蓋,額頭還套上鮮豔惹眼的螢光髮圈,全身裝扮無拘無束顯然在搞時尚,和我像是兩個世界的人。或許也發現我總在這家咖啡館讀《金融時報》,金毛哥某次主動介紹自己以前在倫敦政經學院主修應用數學,打滾金融圈幾年後決定追逐夢想轉換到服裝設計,現在肉品包裝區開了間工作室。
當我心底正讚嘆紐約什麼人都有,從前分毛差不得的財務分析員如今可以是花枝招展的時尚設計師,金毛哥得知我打臺灣來後緊接著說自己會講「普通話」,然後開始用中文洋腔洋調地介紹自己事業版圖橫跨太平洋,紐約、上海兩頭跑,甚至妄言漢語和英語最重要,其他語言就甭學了。
還來不及消化眼前這位金毛哥的多重背景,他便留下電子信箱表示可以幫我介紹在找中文人才的金融機構,但等我真的主動聯繫時又音訊全無。後來在咖啡館巧遇,他卻也能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與我話家常,看來是相當嫻熟交際應酬,難怪可以在紐約恣意穿梭金融與時尚兩大產業。
好萊塢名流在紐約喜歡落腳西村,我也曾在這家咖啡館巧遇奧斯卡影后。某次發現隔桌斜對角一身輕便運動裝扮的女子有點眼熟,新聞人的敏銳直覺告訴我可能是是希拉蕊‧史汪。但礙於身後有面鏡子反射,不方便直接用手機叫出照片比對,直到女子出去接電話,其他客人紛紛激動詢問與她同行的友人我才得以確認。
我對希拉蕊‧史汪的印象都來自奧斯卡頒獎典禮,原以為她是位高大魁梧的女子,結果本人出乎意料嬌小纖細。由於與影后距離近到隨時可以伸手摸一把,我一直觀察她的一舉一動,有幾回還四眼相交,卻也意外發現大明星有點跩,不是非常友善。
她小姐一進這家咖啡館便理所當然地要求店員換掉播放中的獨立搖滾,看得我一愣愣想說是誰這麼膽大,因為就連法國女子都不曾限制員工該放什麼音樂。不過這不打緊,某些時候我也有衝動想拜託工讀生不要一直放告示牌排行榜的流行歌曲,畢竟不合適的音樂足以毀掉一家咖啡館的質感。
比較令我訝異的是雖然貴為兩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影后舉手投足卻流露擔心大家認不出她是名人的焦慮;偏偏紐約客街頭巧遇明星早已習以為常,各個都沉著以對,她只好不斷透過各種誇張的肢體動作昭告天下這裡有位好萊塢明星。然而好不容易有位中年婦女要求合照時,她卻又端出明星架子才欣然答應,看得我倒胃至極。

從白髮奶奶、綠髮奶奶、基金經理人、時尚設計師到奧斯卡影后,在這家咖啡館遇到最令我津津樂道的人,卻是一位看似再平凡不過的年輕男子。
某次扛著一本教科書準備到這家咖啡館啃一下午,當我把課本放到一張空桌時,隔桌的年輕男子和他女友對看一眼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我以為占用了他們的空間急忙道歉,沒想到他女友說:「不是,是我男友在你課本的出版社當線上講師,而且你看封面那張照片,右邊的正是我男友。」
我邊對照,男子邊滿臉通紅和我招手,雙方都不敢相信居然會發生這麼巧的事!我趕忙翻開課本請他在上頭簽名,其他客人也湊熱鬧地問發生什麼事。男子看來生性害羞,反倒把課本闔上,在照片中他那方圓的額頭上刻下名字縮寫,開自己一個玩笑。
點餐時餘光掃到男子在座位上興奮地拿著我的課本合照,我告訴他這本書寫得很棒,受益良多;男子臨走前於是留下一枝那家出版社的原子筆,幽默表示用它考試能幫助我考高分。後來上網搜索發現人家可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紐約果真人才濟濟。
我非常珍惜公寓附近有這麼一家法國女子經營的咖啡館,不僅餐點美味實惠,更認識了形形色色的紐約客。縱使還是會不耐煩有時一份三明治要等個十來分鐘,但若講求高效率,我想去星巴克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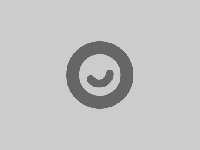










讀者迴響